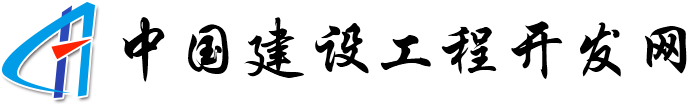與“天一案”不同的是,此次耽美作者被拘捕的起因是同為耽美文學寫手的另一同行的舉報。被拘捕的“深海”與舉報人“燁風遲”曾因彼此作品是否涉嫌抄襲而在網(wǎng)絡論戰(zhàn),但這場本來發(fā)生在二次元世界的“互撕”卻以“燁風遲”向公安局舉報“深海”寫作出版色情作品獲利而收場。借由舉報、借由公權(quán)力的介入,“燁風遲”最終扳倒了在耽美文學圈里排名和段位遠在其之上的“深海”。
“燁風遲”舉報“深海”的“精準謀劃”似乎是受到天一案的啟發(fā),而耽美圈中也的確風傳,在天一案后有關部門出臺了鼓勵舉報此類作品、甚至對舉報行為予以獎勵的規(guī)定。撇開舉報人“燁風遲”是否違背道德底線不談,如果真的如耽美圈所傳,有關部門的確通過獎勵舉報耽美作品的方式來對文化市場予以整治,那么觸動我們思考的問題就是:法律該鼓勵舉報嗎?
二
自諸子百家起,是“親親相隱”還是“大義滅親”就成為我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恒久辯題,其背后所蘊含的正義與倫理的沖突張力在現(xiàn)今的法律中仍有體現(xiàn)。
但法律是否應該鼓勵舉報,這個問題在不同場域下顯然應有不同答案。在有些場域,舉報不僅應該鼓勵,甚至被作為法定義務,典型的例如在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的“強制報告義務”,即醫(yī)療單位、學校等機構(gòu)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強奸、猥褻、虐待、遺棄、拐賣、暴力傷害等傷害時,有義務向有關部門報案的義務。這里的強制報告義務,是法律為特別保護未成年人免受他人尤其是親屬的身體和精神傷害而進行的制度安排。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法律是否該鼓勵舉報在不同場域應有不同回答,但鼓勵舉報似乎正在成為目前各領域為高效管理而慣于采取的方式。于是,因舉報而引發(fā)的問題也在不同場域下以不同方式予以呈現(xiàn)。
以筆者熟悉的公法領域為例,近年來,因舉報投訴所引發(fā)的濫訴已經(jīng)成為困擾行政訴訟和審判的一項難題。這項難題產(chǎn)生的根源同樣在于行政法律規(guī)范中大量存在的舉報投訴條款。而在行政管理領域通過鼓勵舉報來表達訴愿、監(jiān)督公權(quán)又是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tǒng),因此,最初公法領域的舉報對象主要集中于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法律依據(jù)在于憲法第4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quán)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quán)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鑒于舉報在監(jiān)察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所發(fā)揮的積極作用,舉報范圍在此后開始大幅鋪開,并迅速拓展至大部分的行政管理領域。在一般性行政法律規(guī)范中,例如《海關法》、《產(chǎn)品質(zhì)量法》、《安全生產(chǎn)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許可法》等等,我們幾乎都能找到舉報投訴條款。在這些法律規(guī)范中,舉報對象的范圍也早已不限于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而是延伸至所有的違法單位和個人。任何人發(fā)現(xiàn)他人違法,都可向行政機關舉報,行政機關也有義務對這些舉報予以答復和處理,舉報也儼然成為行政機關重要的管理尤其是市場監(jiān)管手段。
對舉報投訴的倚重的確為執(zhí)法任務繁重、財力人力有限的行政機關提供了違法線索來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行政執(zhí)法能力的不足。但就在舉報投訴數(shù)量不斷攀升之時,另一問題同樣接踵而來:鑒于舉報數(shù)量的激增,行政機關不可避免地無法予以及時答復,其答復處理亦在很多時候無法滿足舉報人的訴求。此時,舉報人針對行政機關的拖延答復或是處理不利又會轉(zhuǎn)而去尋求司法救濟,即以受理投訴舉報的行政機關為對象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并借由法院來敦促行政機關履職。這種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行政訴訟中舉報投訴案件數(shù)量的激增。
而法院在處理數(shù)量眾多的舉報投訴案時,同樣面臨如何平衡保障訴權(quán)和防堵濫訴的選擇兩難:如果限制舉報投訴人的原告資格似乎就是在傷害舉報投訴權(quán),而且也與行政訴訟不斷放寬原告的趨勢不符;但如果對其不予限制又勢必造成相關案件的泛濫。據(jù)此,舉報投訴案件的激增、行政機關的處理不利最終轉(zhuǎn)化為訴訟難題而被拋向法院,并以“舉報投訴人是否具有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方式在法律理論和法律實務中予以呈現(xiàn)。
針對上述問題,法院最初的做法是通過指導性案例確認:舉報投訴人惟有為保護自身合法權(quán)益的目的投訴舉報,始具有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反之,如果舉報投訴人并無自身權(quán)益受損,而只是為公益維護的目的進行舉報投訴,就不具有原告資格。
這種區(qū)分處理的方式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的行政訴訟主體仍舊是保護個人利益,它原則上并不允許個人代表公益提起公益訴訟;而另一方面也是借由“私益舉報人”和“公益舉報人”的區(qū)分,防堵那些因為舉報投訴制度的推廣普及產(chǎn)生的大批“職業(yè)舉報人”。而這一點顯然是法院在參酌舉報實踐后更重要的考慮。
因舉報的大幅鋪開所產(chǎn)生的職業(yè)舉報人的前身,就是民事領域尤其是消費者保護領域中的職業(yè)打假人。他們在與商家的長期周旋中發(fā)現(xiàn),與其將精力耗在跟商家的死磕上,還不如掉轉(zhuǎn)矛頭,借由向有監(jiān)管職權(quán)的行政機關舉報而將矛盾轉(zhuǎn)移給行政機關,并通過行政機關向商家施壓來達到自己的訴求;而如果監(jiān)管機關的處理不符其要求,再將監(jiān)管機關訴至法院。
行政審判的這種區(qū)分處理后來又被吸收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12條第(五)項,“為維護自身合法權(quán)益向行政機關投訴,具有處理投訴職責的行政機關作出或者未作出處理的”,屬于“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具備原告資格。
上述規(guī)定表面來看似乎能夠防堵職業(yè)舉報人進入訴訟,立法者也寄望于通過這種做法遏制舉報投訴領域的濫訴,但現(xiàn)實卻是,行政訴訟中的舉報投訴案件數(shù)量的居高不下并未因上述區(qū)分處理而獲得有效緩解,相當大部分的司法資源仍舊被舉報投訴案件所占用。究其原因又在于:
其一、所謂“為維護自身合法權(quán)益”的標準在實踐中極易達到,即使當事人本質(zhì)上屬于“職業(yè)舉報人”,只要他通過簡單的、數(shù)額較低的購買就能與“違法第三人”發(fā)生商品消費關系,就能夠主張其舉報投訴是為維護自身合法權(quán)益;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因為法律對舉報投訴的鼓勵和推廣,使人們在與他人陷入民事糾紛時,很容易就想到借由公權(quán)的介入而向?qū)Ψ绞海M而更高效便宜地滿足其私人訴求,“公器私用”也因此不可避免且不斷蔓延。
行政權(quán)設定和行使的初衷都在于公益維護,而非是為特定人的個人目的的達成,公器私用顯然與行政權(quán)力發(fā)動的初衷不符。除此之外,借助公權(quán)而達到個人目的的做法更危險的后果是,它帶來了民事關系和行政關系、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之間界限的消弭。借由向行政機關舉報,幾乎所有的民事糾紛最后都有可能演變成行政糾紛,原本是雙方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關系最后都有可能可能演變?yōu)榘姓C關在內(nèi)的三邊關系,民事關系和民事訴訟也最終可能被行政關系和行政訴訟所徹底吞噬。
為行政訴訟中“舉報投訴人”資格的澄清,學界和實務屆付出了可觀的努力,其目的都是希望為此問題尋獲一種穩(wěn)定清晰、具有說服力的判定規(guī)則。但如果我們將目光向行政過程的前端追溯就會發(fā)現(xiàn),造成今天這種司法困局的很大原因就在于行政管理領域大量舉報投訴條款的存在,就在于我們的行政管理法律規(guī)范是相當鼓勵舉報的。
我們在設置舉報條款時,基本思路無非是讓壞人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再無處遁形,但卻未意識到,舉報條款更像一把雙刃劍,它有可能節(jié)約行政成本、促進公眾參與,但另一方面它同樣會為借舉報謀取私利、打壓他人提供空間。如果對舉報一邊倒地鼓勵而不加任何防御,其所滋生公報私仇和公器私用將無法抑制。
現(xiàn)代行政演進到現(xiàn)在,我們本應該倚重更科學客觀、 適宜開放的管理方式,但我們的管理思路卻似乎仍舊停留在鼓動群眾揭發(fā)壞人的傳統(tǒng)單一模式之下。這種舉報模式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為行政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其所引發(fā)的舉報濫用和公私不分,卻同樣嚴重傷害了行政能力,浪費了公共資源,并最終危及整個社會的互信機制。
三
再回到耽美作者“深海”和“燁風遲”所涉的刑事案件。在細致描述兩人纏斗的文章“卷入女兒耽美舉報案的武大教授”中,有一個細節(jié)讓人不寒而栗,“燁風遲”曾威脅“深海”在高校任職的父親,“大學尤其是985,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不是學生而是老師,論文篇數(shù)不夠,要倒霉;學生投訴,要倒霉;尤其現(xiàn)在反腐查的嚴,多買一支筆都要倒霉的”。不得不說,“燁風遲”是深諳舉報規(guī)則的,而其對高校教師噤若寒蟬的描述又何嘗不是活在舉報陰影下的每個個體的可能圖像?
從形式法治的角度,我們似乎無法指摘舉報刑事犯罪的“燁風遲”,她從天一案中獲得刑法知識的有益啟發(fā),并通過向司法機關舉報而使在形式上看來的確違法的“深海”最終被羈押。但從其與“深海”的網(wǎng)絡罵戰(zhàn)和之后的糾葛中,又有誰能真正確信其舉報行為就是為維護“違法經(jīng)營罪”所保護的市場秩序呢?又有誰能真正認同其行為的正當性呢?
“深海”因?qū)懽鞯⒚雷髌范孀铮谶@個刑法規(guī)范嚴重滯后于現(xiàn)實發(fā)展,忽視現(xiàn)實世界的價值多元和法益多元的時代,的確又是一起令人唏噓的個體悲劇。與天一案一樣,“深海”涉罪所引發(fā)的震蕩再次提醒我們,法律或許不應是多數(shù)人為價值觀念的整體劃一而對少數(shù)群體施以影響和作用的手段。對于那些小眾群體,對于這些群體的藝術判斷和情感體驗,法律理所應持有的更多的寬容和體諒。但現(xiàn)代法律除需寬容少數(shù)人的價值取向外,也許還應對大多數(shù)人都尊重的良善美德同樣予以認同,其中當然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和體諒,包括不隨意舉報揭發(fā),不利用公權(quán)打壓他人作為人的基本底線。
從這個意義上說,“深海”因同為耽美文學的寫手舉報而被拘捕,也同樣以相當極端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當法律并不寬容少數(shù)人,當公權(quán)并不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和尊重時,它又會在多大程度上激發(fā)甚至釋放出人性的卑劣和幽暗。在我們的想象中,同為少數(shù)群體中的一員,“深海”和“燁風遲”彼此間理應擁有更多的理解和認同。這樣的群體成員在面對多數(shù)價值和多數(shù)意見時,更易抱團取暖而非相互傾軋。但“燁風遲”打破二次元行為界線的做法卻再次證明,當法律縱容甚至鼓勵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jiān)督和彼此舉報時,所有的底線可能最終都會被突破,所有因各種價值選擇和情感認同而積聚起的群體也輕易就都會崩塌瓦解。
“釋放無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這就是我們?yōu)橹鞈俣秩f般無奈的人世間”。法律沒有辦法改變?nèi)诵裕诿鎸碗s人性時,卻應該對其有所體察,并應該致力于使其規(guī)范能有助于人性的提升和良善的促進。相反,如果法律本身會激發(fā)甚至利用人性的卑劣和幽暗,那么其正當基礎也就令人懷疑。從這個意義上說,各個領域盛行的舉報規(guī)范以及其背后體現(xiàn)的鼓勵趨向,其是否合理的確值得我們深思。